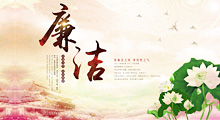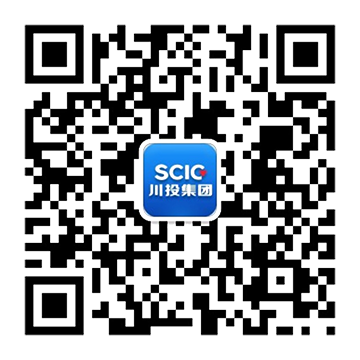今年以来,至少已经发生两轮煤、电双方尖锐的矛盾对立,电力企业的煤炭库存告急的消息频传,而煤价则迭创新高,电力企业亏损的声音更是叫遍几乎所有电厂。国内比煤荒更严重的,则是由于缺煤导致的拉闸限电——电荒。
造成煤、电矛盾激化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半拉子的市场化开放。1992年中国放开煤价之后,电价就没有同步开放,结果当年煤炭价格迅速飙涨,以至于国家对于合法和非法小煤矿的开采,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求煤炭产量的快速增长来抑制过高的煤价。随着国家经济的硬着陆、紧缩政策起到效果,需求被极大压缩,结果1996-1997年全国数以十万计的煤矿产量过剩,煤价一落千丈,煤炭工人也成为最苦、最累、收入最低的一个群体。2002年开始,中国再次放开煤炭指导价,于是2003年中国开始进入另一轮煤价飙升期。为此,2004年尖锐的煤电矛盾促使了煤电价格联动政策的出台。不过当年只有最高5%的通胀情况下,电价还可以上调;但在2008年通胀水平高达7%-8%的情况下,调升电价几乎成为政治禁忌。这种背景下,电厂亏损的声音遍地都是就不令人奇怪了。
虽然中国从十年前就开始推动电力体制改革,2002年又进一步强化了厂网分离,并锐意推动电力产品竞价上网,但电价市场化在十年之后仍旧是纹丝不动。煤电市场半拉子开放的结果就是:经济景气周期的时候,煤炭成为紧缺资源,煤价大涨,电价却受到高度管制,电力生厂商自然没有更大动力来增加生产供应,电力紧张甚至短缺也就随即而至。这种“电荒”就是安邦分析师屡次提到的“机制性电荒”。
不过,煤电市场的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国内煤炭市场从1992年就开始号称市场化了,而实际上,电力企业仍旧享有庞大数量的“计划煤”。拿中国神华这家最大的煤炭生产商来说,根据其2007年年报,在去年煤价飙涨的时候,年报披露的神华国内加权平均煤价涨幅仅约1.9%,从2006年的296.1元/吨上升到301.8元/吨,比市场平均煤价低了25%以上。因此,所谓的电力大面积亏损,电力生产成本大幅飙升,明显有被大幅夸大的嫌疑。
我们不能否认的是,电力企业在中国市场上所拥有的强势地位,即便是煤炭如此紧缺的情况下,仍然没有任何一家煤炭企业敢于得罪电力企业,电力企业仍旧可以享受2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账期。这种地位,我们也可以从一些质疑文章中看出:每次煤荒、电荒出现之后,就常有媒体发布电力企业可能在敦促政府提高电价的质疑文章。坐大者,总是容易受到别人质疑的。而在微观层面,电力企业相比煤矿企业的地位也可以显而易见地观察到。无论谁到煤矿与电厂同在的地方,几乎都能发现大型超市总是开在电厂职工附近,而极少在煤矿工人附近,因为这些商业经营者都知道:电厂职工的消费能力,要远超过煤炭企业的职工,哪怕煤价涨得再高。
在这样的国情下,电力体制改革的阻力事实上正是来自于电力企业本身。有谁愿意在自己是市场“老大”的情况下,来改革“自己”呢?这就是电力体制改革进展极为缓慢的根本原因。然而,在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和能源需求面前,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情况将不得不作出改变。
今年年初开始电力企业人事调整时,我们就曾经指出,这可能是旧电力体制下的最后一波人事调整了,此后真正的电力体制改革可能会在三五年内展开。然而,事态进展得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据电力企业“龙头大哥”华能国际公司的公告,该公司董事长已因工作调动于6月2日提交辞呈。而来自《财经网》的最新消息则称,被海外媒体称为“亚洲电王”的华能国际董事长李小鹏将被调往山西担任副省长。由于人事调整在中国从来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因而这则信息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猜测。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电力企业高管被调往煤炭大省,可能是政府对市场释放了一个极为强烈的信号:煤电矛盾绝不能如此继续下去。事态如果沿此路线发展,不排除未来电力系统继续爆发人事“地震”的可能,而电力体制改革、竞价上网、输配和供电资产分离等各类市场化措施,都可能在此后提速。一场真正可以“伤筋动骨”的电力体制改革,可能正在快速酝酿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