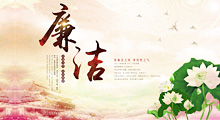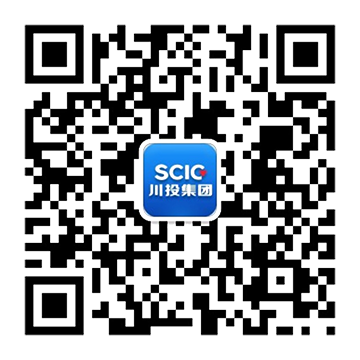3年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蜚声国际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这样描述越来越“扁平”的世界:市场、劳动力和产品都可以被整个世界共享,一切都有可能以最有效和最便宜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无可阻挡。
正是借助这种“无可阻挡”的全球化,像中国这样的亚洲经济体成功地承接了欧美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市场格局。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消费是世界其他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食粮”。这种消费意愿和消费规模的膨胀,甚至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数据显示,从1994-2007年的14年间,按实值计算,美国实际消费需求的趋势增长率每年高达3.5%——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对现代史上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这都是一场最盛大的消费狂热。同一时期,美国实际可支配个人收入增长平均仅为3.2%。在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看来,依靠发达的金融创新和宽松的监管体系,美国消费者似乎发现了一种新的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术以代替传统的收入型储蓄。这种资产型储蓄,先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股票质押,然后是本世纪上半期的房产抵押。储蓄模式的调整,一方面支撑了美国狂热的消费,并轻而易举把其储蓄率推低至零点甚至是负值。近20年来,美国的储蓄率节节下滑,从1984年的10.08%到1995年的4.6%,2005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另一方面,美国消费者也为此背负了创纪录的债务。截至2007年底,美国家庭部门负债率飞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比10年前上升了40%。
如果美国的资产价格一直处于上行通道,一切问题都可能被掩盖,但始于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次贷危机以及目前正在全球肆虐的金融危机,完全刺破了这个巨大的泡沫。按照罗奇的观点,美国由收入型储蓄向资产型储蓄的转型失败了,美国消费者可能将不得不接受其传统消费模式行将终结这一现实,“中国制造+美国消费”模式的调整已经拉开序幕。
美国消费主导型的增长将走向何方?货币主导型的出口增长会重现光芒吗?尽管这一结论现在看来仍显得扑朔迷离,但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正在“班师回朝”,传统产业以及由此带来的出口增长正在慢慢复苏。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 Motors放弃了原来在泰国生产电池、英国组装,然后运回美国的生产流程,取而代之的是,将所有生产环节全部集中于加州总部周围。美国家具经销商过去习惯于将木材从美国本土运到中国,加工成沙发、橱柜、桌椅后再返销美国;现在这些木材直接在弗吉尼亚或北卡莱罗纳进行加工制作。过去5年美国商品出口交易额成长80%,由2003年第1季的1760亿美元,成长至2008年同期的3160亿美元。以钢铁业为例,海外订单增加,使得美国钢铁业由5年前亏损4200亿美元,剧增至去年获利近8800亿美元。
全球运输成本的高企、新兴市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正在为这种模式的调整推波助澜。加拿大投资银行CIBC World Markets发布的报告指出,航运费今年以来上涨的幅度相当于平均提高了9%的贸易关税。大型集装箱运输船队选择降低20%的运速以控制燃料成本。“运输货物的成本而非关税,才是全球贸易的最大挑战。”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拉近其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薪资距离。在中国,近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更加显著;在越南,劳动力成本正在以每年15%的速度上升;东欧国家的劳动力也不再“廉价和充足”。
除了上述投资领域的“逆向转移”,美国人的消费模式和消费意愿的变化,则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去年以来,美国人的好日子似乎已经彻底结束,接连遭受了次贷危机、国际油价上涨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等多个因素的打击,其最大的影响是打破了美国人的资产储蓄型模式,迫使美国人开始学着节衣缩食。从去年次贷危机以来,已经有多种信息显示,美国人在减少消费,并开始改变个人消费模式——高耗油汽车不再时髦,美国人外出长途旅行开始减少,奢侈消费也开始减少。此轮金融危机更是毁掉了千万人未来几十年的消费支出计划,甚至可能使下一代美国人在不同的消费观念中成长。消费模式具有强大的惯性,其转型并不容易,但一旦转变发生,再恢复过来也不容易。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美国消费的转变,对于出口导向型的亚洲意味着巨大的转变,而中国将会首当其冲。
经济模式调整如何影响另一端的中国?尽管中国的外贸出口数据依然可观——1-8月出口累计增长22.4%,但如果刨除掉人民币升值和价格上涨因素,实质的出口增速可能只有个位数。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速的下降更是惨不忍睹。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已经从2006年的24.9%下降至2007年的14.4%,2008年1-7月更是下降至9.9%。既然全球化塑造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那么,“美国消费”的调整与转型必然带来“中国制造”的环境的深刻变化。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全球经济面临规模巨大、历时可能很长的再平衡过程,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由收入型储蓄向资产型储蓄转型的失败,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模式的转型。我们难以预期这个过程会持续多久,程度有多深,但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对由此引发的外需环境的巨大转变做好准备。也许,只有中国内需市场的极大启动,才能迎接这种变化。